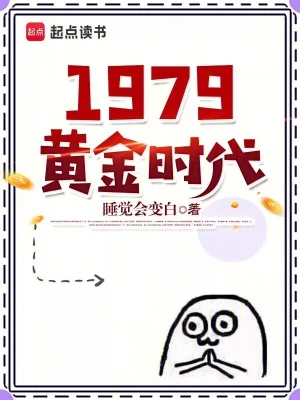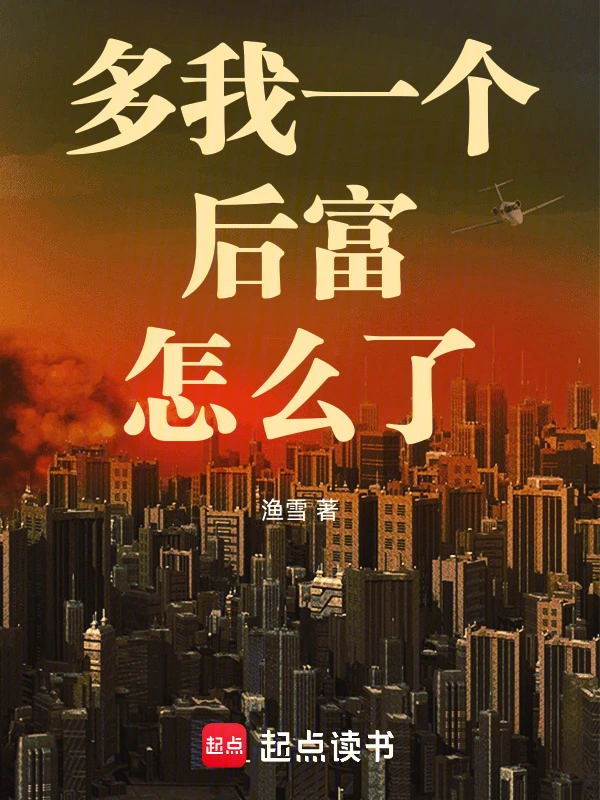第233章 升了半级
家窑,史家窑,西窑沟…等等等等。不管哪一处,都比老窑头更适合烧瓷器:至少交通便利,煤矿铁矿没那么集中。
在场的都是行家,甚至是专家,不管换成谁,都不可能因为这个“窑”字,跑来这里找瓷窑。
但偏偏,真的被他找到了不说,还这么大?就感觉,那个林思成长了透视眼一样?
最怪的是:他们拿着白瓷样本,找到的却是黑瓷窑?
王所长又叹了口气:怪的何止是这一点?
凑巧碰到了几块瓷片,就敢断定运城有古窑,就敢和市里谈条件?然后不惜成本的探查,更不计代价的征集相关文物?
只是征集了很少的一部分,基本没有做什么前期调查。就敢断定窑址在河津?然后,直接就调来了田野所和考古队,而且来的是最为专业的省所和省队?
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没有任何文献相关,地面上没有任何相符合的遗迹。就跑来了老窑头。然后,硬是围着两座没什么参考价值的缸瓦窑勘察了半个月?
结果没出意外,什么都没发现。
扪心自问,不怪当地不重视:这些人从开始到这一步,所有的行径都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有点可笑。
但谁都没想到,奇迹出现了:
最后一天,那位林老师围着河道和岸台转了几圈,发现了这几个坑。然后一钎子下去,就探到了木灰池。
这是什么概念,这又是什么概率?按道理,这是压根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扪心自问,换成他,他绝对找不到。
再把这些疑点综合一下,王所长就觉得:好像那个林思成提前就知道这里有窑址?
他又打量了一圈:“刘馆长,你们当时有没有问过,那位林老师是根据什么依所,判找到的木灰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9页 / 共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