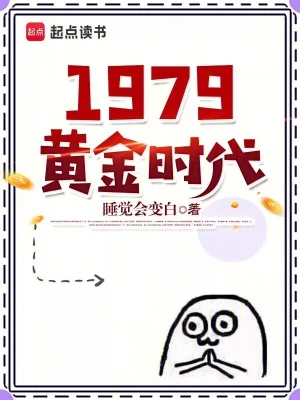第二百八十三章 营养问题
基因驱动下去拼命摄食这类食物。
只有在摄食变得容易,人的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这种基因驱动力才体现出它的负面效应。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日常饮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基因的惯性是强大的,与有关饥饿的记忆一起,形成了很多地方菜的特色。在清代开始逐渐走向成熟的各地方菜系,无论南北,大多尽力做到了肉管够、菜管够、油水管够。这是中国传统美食经营者最大的诚意。
以今天的眼光看,毋须讳言,它们是不健康的,但如果不是天天这样吃、顿顿这样吃,也多半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纵向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历史上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不是这样的,吃什么,吃多少,首先要看能获得什么,获得多少。
夏商之前没有主食副食的差别,有什么吃什么。夏商及夏商以后,开始稳定地以谷类为主食。粮食可以说一直是国家和家庭的头等大事。
先秦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到两汉的时候,社会上层开始出现一日三餐,到唐宋,普通人才普遍吃上三餐,加了一顿午餐。
中国太大,发展极不均衡,再加上古代战争、灾害频繁,所以普通人三餐或两餐实际长期并行,甚至同一个地方,某些时期是三餐,某些时期又是两餐。混一顿饱饭真不容易,这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水平上的。自秦汉以后两千年间,农业技术没有根本变化,粮食生产量虽有提高,但都很有限。
统计显示,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110.0公斤,比1956年下降了36.6%。粮食消费下降,是粮食消费在整个食物消费中占比下降了,这段时间里肉蛋奶等副食消费占比提升了。
在古代,盐长期是国家控制的专营物资,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明朝,盐还实施配给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盐长期都是宝贵的必需品。盐业也因此是最容易出富商的行业。对于地处边远山区的人,盐能满足生理需求就不错了,不要说吃得那么重口。所以出现了西南山区地方饮食以酸当盐,以辣代盐,以草木灰代盐的现象。这些既是美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艰难历史的见证。
关于吃肉,更是一个巨变。肉在古代社会上层供应是不错的,比如北宋宫廷喜欢羊肉,仁宗时期一天宫里就要宰杀280只羊。但是民间并不容易吃肉,有贫穷儒生为了吃羊肉,把苏东坡给自己的书信拿去换了十几斤羊肉,黄庭坚因此戏称苏东坡的书法为“换羊书”。
根据《大西洋月刊》2018年的数据: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人的肉类消费量增长了7倍;1980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沦为男主玩物的绿茶女配H
- 《打脸女配高攀上男主之后H》if线又称原著篇 没有穿书的魔幻,走现实暗黑、强制路...
- 126489字09-29
- 八十年代渔猎日常
- 2350330字08-02
- 1979黄金时代
- 3433318字06-06
- 杀人狂魔的MAOA暴力基因
- 父母杀人犯,湛娄生来就携带着犯罪基因的恶人,叔叔拿走了他的救济金,将他送往国...
- 118379字09-14
- 勾引闺蜜男友(NP)
- 闺蜜长得美,校草们接二连三追。高考都有别校校草舔着脸上门,拿着笔在手上求着留号...
- 41348字04-12
- 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3121363字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