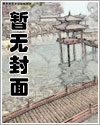买活 第612节
较费力,没有继续做文人戏曲那么轻松罢了。
可倘若从道统的角度来看的话,如今是百姓的年代,文艺作品也该反映的是百姓的娱乐爱好,如果不能完全融入百姓,其实机体将出身、兴趣、爱好都完全和时代需要错配的这些人,自发地排挤出去,也只是时间问题,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站在时代的角度来说,区别不大,迟早总会发生。
该来的终于来了,也一定会来,不管有没有她参与,都是一样,没准叶瑶期的观察,还能降低不少六姐对沈家的疑虑和猜忌——如果真实并不太丑恶,那么真实总是好的,想象力的泛滥才最可怕。姨母的结局,说不定就因为叶瑶期的观察,而会更体面一些。
至少,叶瑶期本人是如此坚信的。因此,她不但没有心虚内疚,反而理直气壮,带有一种以功臣自居的自信从容,主动地关切起了沈曼君的情况来,“姨母那边……难道是风雨飘摇、败局已定了?她就没想过做一次还击吗?她如此消极,只怕……许多叔伯姨姐,也很着急失望吧?”
不说这几个同父母、同(外)祖父母辈的近亲,五服内外,出身吴江几姓的才女,加在一起都有数十人了。要说这些人都情愿接受失败,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如今市面上很多自发地为姨母辩解的文章,文笔雅驯、态度恳切而观点中肯的那些,很多都是她们的手笔,只是找了别的名字发出来而已。叶瑶期认为,倘若姨母度过了这个劫数,之后《买活周报》也会立刻更改制度,确保将来外人无法如此容易地抓到把柄。很显然,现在她的这些亲戚是已经学乖了。
相关小说
- 金牌床上补习/现代/SM/H
- 金牌补习教师李雩与即将分手的特种兵炮友车震时不小心被学生家长发现,原以为会被人...
- 2221747字12-13
- 失贞后被青梅竹马叼回窝里调教成小母狗
- 林欣欣被自己的闺蜜下药,送上了系主任的床。从此以后,林欣欣被系主任用裸照威胁,走...
- 4079204字12-10
- 林可可的私生活
- 初入职场的法律系学霸校花,一步步沦为带教律师、老板、合伙人、客户等人的泄欲工具。
- 882439字03-03
- 下定决心要孝敬爸爸的好女儿
- " haiTangshuwu.COm 陈静,陈健的女儿,为了让陈健能从母亲离世的阴霾中走出,...
- 32129字04-29
- 吹拂雨沙沙
- 车在红绿灯前停下,朋友指向车窗外:你们班的。裴琤从副驾驶侧头。两手提着超市购物...
- 84029字01-02
- 催眠玩弄体院男神(总攻、NP)
- 催眠玩弄体院男神(总攻、NP)笔趣阁,催眠玩弄体院男神(总攻、NP)sodu,催眠玩...
- 118201字05-18